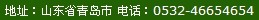|
转自:互联网胡萝卜 原创:谢君泽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犯罪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 央视不代表权威,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诚如年辽宁春晚《吃面》小品中宋小宝所说: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人们对于春晚,人们对于“海参炒面”,其实只是需要一个“完美的解释”。与此相同,快播案定罪是必然的,但我们所寄望的是司法者能否给予人们一个“完美的解释”? 快播案中,很多问题都需要司法者给予解释。但是,笔者认为,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快播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传播”?是否属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所规定的“传播”?前者是本案公诉最为关键的法理基础,后者则为本案公诉最为直接的法律依据。“传播”概念的法律界定直接关系到快播案的定性!至于后续关于快播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及能否构成共犯等争论,都只是在此基础上的法律演绎。 “传播”的多重概念:回归法律行为的视角“传播”二字的含义是十分复杂的。在传统语境下,“传播”二字就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内涵。将“传播”二字放在政治语境下理解,它是指“观念或精神内容的传递过程”;将“传播”二字放在公共社会语境下理解,它可以理解为“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将“传播”二字放在信息系统语境下理解,它又是指“信息从信源经过信道到达信宿的传递过程”;将“传播”二字放在新闻媒介语境下理解,它又凸显出“传播媒介”的语义……而,目前最广义的“传播”概念,是指信息的传递。它既包括接触新闻,也包括表达感情、期待、命令、愿望或其他任何东西。 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由于网络技术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技术,这无疑加剧了“传播”概念的混淆!即,“传播”二字有了最新的语境,就是传播技术的语境。当然,笔者认为,有一点是所有人可以达成共识的:网络技术的出现,对于人们“传播”观念的冲击,一定是颠覆性地。势必地,网络技术的出现也一定会促进人们对“传播”概念的重新思考。准确地说,是在不同语境对“传播”概念的重新界定。 “传播”概念在其他语境下出现混淆,似乎亦无伤大雅。但是,法律作为一门应当十分严谨的学科,笔者认为,法律语境下的“传播”概念是绝不可随意混淆的。尤其在刑事领域,“传播”概念的法律界定直接关系到定罪与量刑,更不可随意而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实践中,不管是立法者、司法者亦或是人民大众,在理解“传播”的法律概念时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掺杂了“法外”的语境。 那么,到底法律语境下的“传播”概念如何界定呢?或者说,“传播”的法律概念如何界定呢?对此,笔者不敢妄谈定论。但是,笔者认为,不管是何概念,只要在法律语境下进行界定,它首先应该遵守法律的基本原理。即,法律是用于调整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社会规范。基于此,笔者认为,观察“传播”的法律概念必须把握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首先放到行为学角度进行思考。法律所要调整的对象,首先应当是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传播”行为是法律评价的第一指标。而像传播效果、传播方法、传播手段、传播方式等,虽然有可能作为法律评价的第二指标从而成为定罪量刑的参考,但绝不该也不能喧宾夺主。因此,笔者认为,法律语境下的“传播”概念,主要是“传播行为”意义上的概念。 第二,必须放到法律关系角度进行思考。由于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是权利和义务,因此,在法律语境下的“传播”概念,或者说“传播行为”的概念,应该主要考察行为人是否有权实施某种“传播行为”,或者行为人是否有义务不得实施某种“传播行为”。即,法律语境下“传播”概念的内涵,主要是指行为人是否具有“传播”权利或者是否具有不得“传播”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层面的内容。 最后,必须遵守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但它并不等同于道德、习惯等一般社会规范。法律规范,作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则,它往往是明确具体的,并且具有严格的内部逻辑结构;它往往预先设定具体的假定条件,并确定满足假定条件的法律行为后果。从规范法学的意义上讲,只有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的“传播”字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传播”概念。 在此,笔者仅就我国现行刑事实体法中的“传播”规范进行梳理。目前,我国刑法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相关“传播”罪名: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刑法第条第1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法第条之一),传播性病罪(刑法第条第1款),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刑法第条第1款),传播淫秽物品罪(刑法第条第1款)。然而,立法者与司法者并未对相关的“传播”概念进行具体明确地界定。这就造成司法实践中“传播”法律概念与“传播”法外概念的混淆。实际上,笔者认为,快播案就是概念混淆的集中体现。 我们不妨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对前述刑法规范中的“传播”概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所有的“传播”一词要么就是与“编造”、“制作”、“复制”、“出版”、“贩卖”等动词并列,要么就是显然的动词词性。笔者认为,这与前述的行为学视角是遥相呼应的。换言之,现行刑法规范中关于“传播”的规定,都是指行为意义上的“传播”。而这种行为意义上的“传播”,也可以从法律关系角度进行理解。即:行为人具有不得实施“非法”传播行为的义务。 至此,不难得出结论,认识“传播”的法律概念,我们应该摒弃“法外”概念的干扰,回归法律的视角,回归行为的视角。 传播行为模式的变化:以历史研究为视角如果说,法律语境下的“传播”概念,主要是行为意义上的“传播”,这种推论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笔者认为,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法律规则,不妨以历史研究的方法从传播的行为模式入手。 在过去,如果甲要给丙传递一封信件,那么甲先将信件传递给乙,再由乙传递给丙。这种方式可以归纳为“人-人-人”的传播行为模式。显然,这种传播行为模式主要是依赖于人,基于人的信赖关系来完成。在这种传播行为模式下,由于乙应当能够一定程度地了解传播的物品,因此,乙作为传播者,应当负有对传播物品及其内容的审慎审查义务。如果乙明知甲向丙传递的是“违禁品”而继续帮助“传播”,则势必要承担“非法传播”的法律责任。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今天,“人-人-人”传播行为模式不再是主流的传播方式。在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大趋势下,像快递公司、物流公司这样的“人合组织”取代了原始的“自然人”中介角色。即,今天的传播行为模式其实已经发展成“人-人合组织-人”的传播方式。形象地说,在今天,如果甲要给丙传递一封信件,甲根本不再需要寻找一个自然人“乙”,而是直接交由快递公司、物流公司这样的“人合组织”来完成。毋庸置疑,社会职业分工使然! 不论若何,在今天,传播者不再是以自然人为代表的“人”,而是以公司、企业为代表的“人合组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快递公司这样的“人合组织”是否应当承担过去“自然人”传播中介所应负担的“审慎审查义务”呢?如果需要承担,“人合组织”对于传播物品及其内容的审查义务是否应当有所减轻?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思考:如果你要传递一个“违禁品”,你请你的朋友代为“传递”与你请快递公司代为“传递”,他们所应负担的“审慎审查义务”是否应当有所不同?根据现行《邮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邮政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并执行邮件收寄验视制度。对用户交寄的信件,必要时邮政企业可以要求用户开拆,进行验视,但不得检查信件内容。用户拒绝开拆的,邮政企业不予收寄。对信件以外的邮件,邮政企业收寄时应当当场验视内件。用户拒绝验视的,邮政企业不予收寄。据此,可以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快递公司这样的“传播者”,所应负担的是一种“物品”本身的审查义务,但不承担“物品”内容的审查义务。然而,实际上,由于采用“人工”方式对物品进行“验视”审查,既费时,又费力。很多快递公司,尤其是民营的快递公司,都是借助于“安防扫描设备”这样的技术设施来完成。显然,职业化的第一目标是提高“效率”。与物品“验视”这种类似“实体审查”的方法相比,利用“安防扫描设备”实施“程序审查”,从效率上讲,明显高得太多。 然而,到了网络时代,不管是“物品验视”或者“安防扫描”,这些方法似乎既失去了效率也失去了效果。所有的“审查方法”都失灵了!这是为什么呢? 从物质观和信息观的角度来观察,不难发现,不管是过去的“人-人-人”传播行为模式,亦或是今天的“人-人合组织-人”传播行为模式,传播行为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仍然停留在“物质转移”的阶段。但是,在网络时代下,传播技术的升级俨然已经带动了传播行为本质的变化,以及传播行为模式的升级。具体地说,在网络时代下,传播行为的本质已然由“物质转移”变为“信息复制”。显然的是,“信息复制”与“物质转移”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此基础上,传播行为模式也业已由“人-人合组织-人”升级到“人-技合组织-人”。这里的“技合组织”,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换言之,“网络平台”取代了“快递公司”的角色,人们“传播”物品或物品内的信息不再需要“快递公司”这种“人合组织”的中介,而更多地寻求“网络平台”这种“技合组织”的中介,以提高传播的效率、降低传播的成本。与“人合组织”相比,网络平台这样的“技合组织”显然有更多的优势。比如,“技合组织”不再依赖于“人力多少”,“技合组织”以“自动化传播”取代了“人工传播”。 那么,我们如何赋予“网络平台”这种新型“传播者”的法律义务呢?显然,过去和现在的传播法律规则只能停留在“物质控制”的目标。然而,在网络技术的影响下,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已经没有了“物品”(载体)的概念,所有的“物品”都全部表现为近乎相似的二进制“码流”。基于此,我们更多要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建立以“数据控制”为目标的网络传播法律规则,而非再局限在以物品“验视”为代表的传统传播法律规则。 其中,由于“网络平台”在新型传播行为模式中位居关键的“枢纽”地位,因此“网络平台”的法律规制是网络传播法律规则的重中之重。具体包括:“网络平台”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数据监管”规则,如何采取必要的“数据监管”措施,如何承担相适应的“数据监管”责任,是为网络传播法律规则之要义。 法律是调整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的产物。笔者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法律规则的技术化与技术规范的法律化必将成为法学研究的长远主题。即:如何使法律规则与技术发展保持相应的对称性和同步性,同步地设置与网络空间中技术现象相对称的法律规则。实际上,笔者认为,快播案的本质问题正是在于:传统的传播法律规则已经无法科学评价网络空间中的新型传播现象。 网络传播的法律特征:以分类研究为方法既然网络时代下传播行为的本质已经升级为“信息复制”的范式,而“信息复制”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传播”,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法律所要调整的“传播”到底是哪些“传播”?技术本身所导致的“传播”是否应当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在此,不妨采取最为朴素的分类研究方法以探究竟。人为传播技术传播VS所谓人为传播,是指反映人的主观意图产生法律行为表达意义的传播。比如,一个人为了某种目的,在网络上上传一个文件或下载一个文件,以实施特定法律行为,进而产生的信息传播。显然,人为传播的典型特点是:具有人的“目的性”和“行为性”。而技术传播,是指由于网络传播本身就是信息复制的技术过程,因此而产生的信息传播。在网络空间中,由于网络技术的特定性,技术传播是一个必然事件。网络空间中的任何信息交换都是技术传播的过程。然而,技术传播又不必然都属于人为传播。 笔者认为,由于法律是用于调整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规范,因此不蕴含人的“目的性”和“行为性”的技术传播,不应纳入“传播”法律概念的范畴。即,不反映人的主观意图和人的法律行为的技术传播,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传播,而只是技术意义上的传播。其实,这种观点与人们所强调的“技术中立原则”是遥相呼应的。 具体地说,前述所说的网络用户上传、下载行为往往是反映人的“目的性”和“行为性”的人为传播行为。但是,在网络数据窃取、网络数据泄漏等网络技术入侵案件中,由于这种传播并非是(持有数据的)网络用户或网络平台的目的行为,因此即使事实上造成信息的大范围传播也不应以传播法律规则进行调整,而应适用另一些专门的“网络行为的禁止性规则”。 主动传播被动传播VS站到网络用户角度而言,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属于主动传播,除非出了前述网络技术入侵的例外。而,站到网络平台角度而言,以提供资源交换为职能的“引导交换型”网络平台主要是被动传播,而以提供网络资源本身为职能的“自供自给型”网络平台则主要是主动传播。 当然,如果“引导交换型”网络平台故意以“网络用户”的匿名身份传播非法网络资源,亦或是明知某“特定”网络资源是非法传播仍纵容传播,则完全有可能产生被动传播与主动传播的竞合,或者产生被动传播向主动传播的转化。因此,就快播案而言,案件中快播是否存在故意以“网络用户”的匿名身份上传非法网络资源,以及快播是否存在对某“特定”非法网络资源的明知,是司法者可以重点青少年白癜风白癜风哪家医院看的好
|
当前位置: 淘宝营销_营销课程_淘宝应用 >349期3从宋小宝吃面到快播案定罪
时间:2017-2-2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国货护肤品全推荐,好用买得到
- 下一篇文章: 不想315被封店扣分的看过来